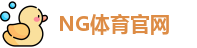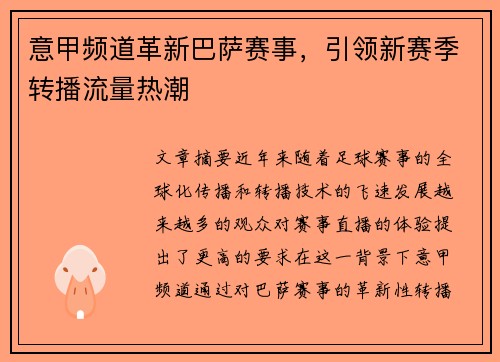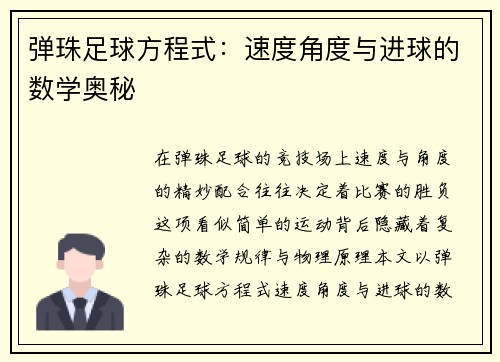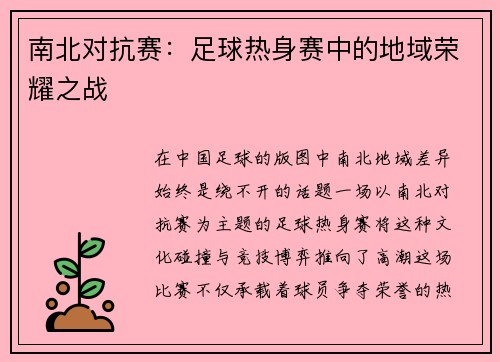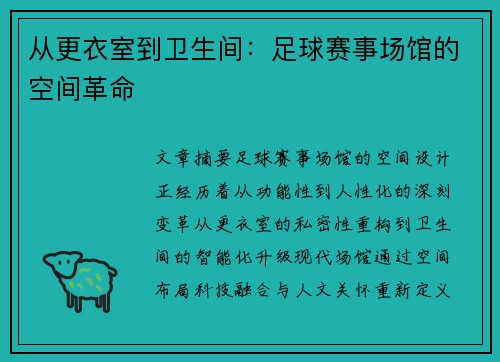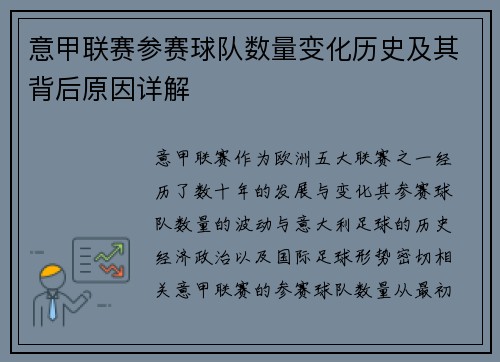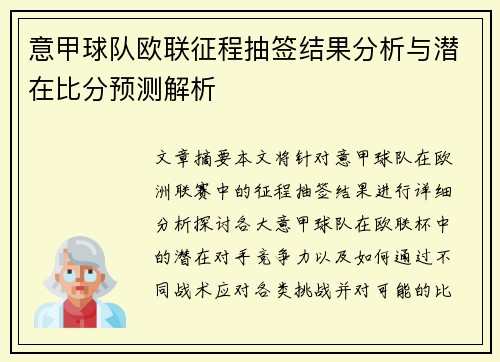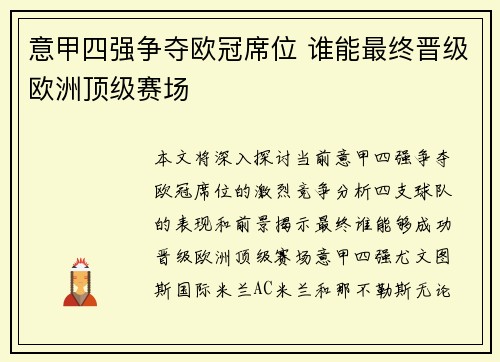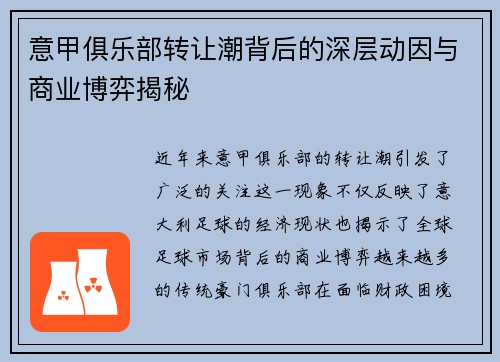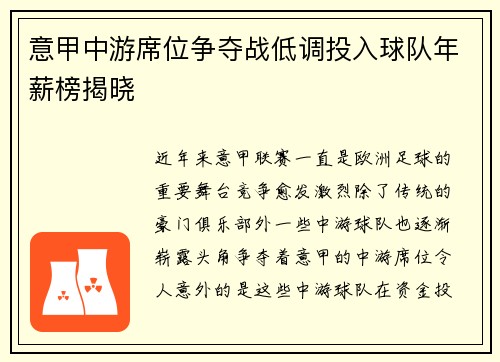在足球场恢弘的灯光下,后摇滚的声浪与人群的呼吸交织成一场超越时空的仪式。《足球场灯光下的后摇终章》以体育场这一矛盾空间为载体,探讨了现代人如何在集体狂欢与个体孤独的夹缝中寻找精神出口。当合成器的轰鸣撞击着看台的混凝土结构,当吉他音墙裹挟着夜风穿透三万人的胸腔,这场演出不再仅是音乐的终结篇章,更成为城市化进程中人类情感的隐喻。本文将从空间重构、声音暴力、群体解构与自我救赎四个维度,剖析这场独特文化事件背后,艺术与现实的激烈碰撞。
南宫体育官网入口1、钢铁穹顶下的空间诗学
足球场本是竞技与对抗的容器,其环状结构天然制造着对立。然而当灯光暗下,舞台光束刺破夜空,混凝土台阶化作琴键般的起伏谱线,整个空间被重新赋义。后摇滚乐队利用场地纵深,将鼓点投射至远端球门,使声波在弧形墙体间折射出立体回声。观众席不再是等级分明的观战台,而成为声音共振的参与装置。

照明系统的戏剧化运用颠覆了体育场的功能性。频闪灯模拟着神经元突触的放电,追光灯在草皮上书写光的乐谱,LED矩阵屏则分解为抽象色块。这种空间异化使得三万人的巨型场馆产生了实验室般的精密感,每个个体都成为声光实验的样本。
更具颠覆性的是观演关系的重构。当乐手隐匿于烟雾与逆光中,当主唱背对观众面向空旷球场嘶吼,传统的表演中心主义被瓦解。观众在明暗交界处既是观察者又是被观察者,体育场这个现代性图腾,最终在声光电的改造中成为存在主义的剧场。
2、声音暴力与温柔共谋
后摇滚的声浪在足球场获得了物理意义上的解放。120分贝的吉他噪音撕裂空气,低频震动使看台扶手持续嗡鸣,这种声音暴力并非破坏性的宣泄,而是创造着集体心跳的生理同步。当失真音墙达到临界点时,许多观众出现短暂耳鸣——这正是后摇美学的终极隐喻:用疼痛确认存在。
温柔旋律的介入方式则充满矛盾。清澈的钢琴独奏通过分布式音响系统,从球场四角同时升起,形成声音的十字包围。弦乐声部通过时间延迟处理,在空间不同位置错位重现,制造出记忆碎片般的听觉蒙太奇。这种温柔不是对暴力的妥协,而是将其衬得愈发暴烈。
最具革命性的是沉默的运用。在某个乐章戛然而止的瞬间,夜风掠过草皮的沙沙声、远处高速公路的胎噪、看台上压抑的咳嗽声全部涌入听觉真空。这种主动制造的声场留白,让三万人在寂静中听见彼此的存在,完成了声音暴力最温柔的共谋。
3、群体狂欢的原子化解构
体育场原本是培育集体意识的温床,后摇终章却对其进行精密解构。通过智能灯光系统,观众席被分割成数百个色块单元,每个区域随着音乐变换光色。当相邻座位呈现冷暖对比,当光波如潮水般在人群中传递,个体的独特性在色彩编码中被强化,群体被还原为原子的集合。
音乐本身的非线性叙事加剧了这种解构。没有传统摇滚的副歌重复,没有明确的情感指向,乐章间突然的变速与变调不断打断情绪积累。观众不得不放弃集体共鸣的期待,转而专注于私人化的感受拼贴。某个中年男子在狂暴的鼓点中想起离婚诉讼书,而少女却在温柔的提琴声中听见skateboard划过沥青路面的声响。
最深刻的异化发生在终章时刻。当所有乐手停止演奏,三万部手机同时亮起,星群般的光点在黑暗中无序闪烁。这个由观众自发完成的行为艺术,彻底消解了集体仪式的神圣性,将现代人孤独的本质暴露在冰冷的夜风中。
4、废墟之上的自我救赎
演出结束后,遗留在场内的不是寻常演唱会后的亢奋,而是类似宗教体验后的精神虚脱。满地散落的荧光棒像电子时代的香灰,被踩碎的塑料杯发出圣餐饼般的脆响。这座刚刚经历声波洗礼的体育场,此刻如同文明废墟的隐喻现场。
人们离场时的姿态泄露了隐秘的救赎渴望。有人故意绕远路穿越整个球场,让鞋底沾上草屑;有人反复摩挲印着乐队logo的混凝土墙体;更多人选择静坐在尚未关闭的应急灯下,用手机录制虚无的黑暗。这些细微的仪式性行为,透露出对瞬时永恒的徒劳捕捉。
最具象征意义的是保安的转变。最初机械执行清场命令的工作人员,最终靠在球员通道口点燃香烟,任由猩红烟头在黑暗中明灭。这个被规训空间的反叛者,在不自觉中成为了整场仪式的最后一位表演者,完成了对体制化日常的短暂超越。
总结:
《足球场灯光下的后摇终章》以近乎暴烈的方式撕裂了现代生活的表象。在声光电的共谋中,体育场这个象征集体主义的空间被解构成存在主义的实验室,三万观众在噪音与寂静的辩证中,经历了从群体依附到个体觉醒的精神嬗变。这场演出证明,当代艺术真正的颠覆性不在于形式创新,而在于其创造情境让人直面存在的荒诞与尊严。
当城市灯光重新吞没体育场的轮廓,那些在回家路上突然驻足仰望星空的人,那些在浴室镜前凝视瞳孔反光的人,仍在消化这场声波地震的余震。后摇终章没有提供答案,但它成功地将疑问种进了三万具躯壳——在这个高度系统化的世界里,我们是否还能在集体轰鸣中听见自己的心跳?这个悬而未决的诘问,或许正是现代人最珍贵的生命体征。